他站在当代思想的地平线上,眺望浪漫主义的余晖
2025年,是美国文学理论家、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巨擘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逝世10周年。这位生于1912年的世纪老人,几乎亲历了整个现代及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衰,但其研究范畴,始终集中于浪漫主义文学。即使在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在北美文学理论界风头正劲的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他也绝少受这些思潮影响。其职业生涯的两部代表性作品,《镜与灯》(1953)及《自然的超自然主义》(1971),显示出理路的连贯性。后者虽写于解构主义的时代,却丝毫没有追逐时髦理论的焦虑。这两部著作都是极为典型的英美学院派写法,围绕着一两个核心意念,论述的丝缕层层缠绕,结成坚硬的块垒。读者可以清晰地聆听到,材料与理论交织形成的思想变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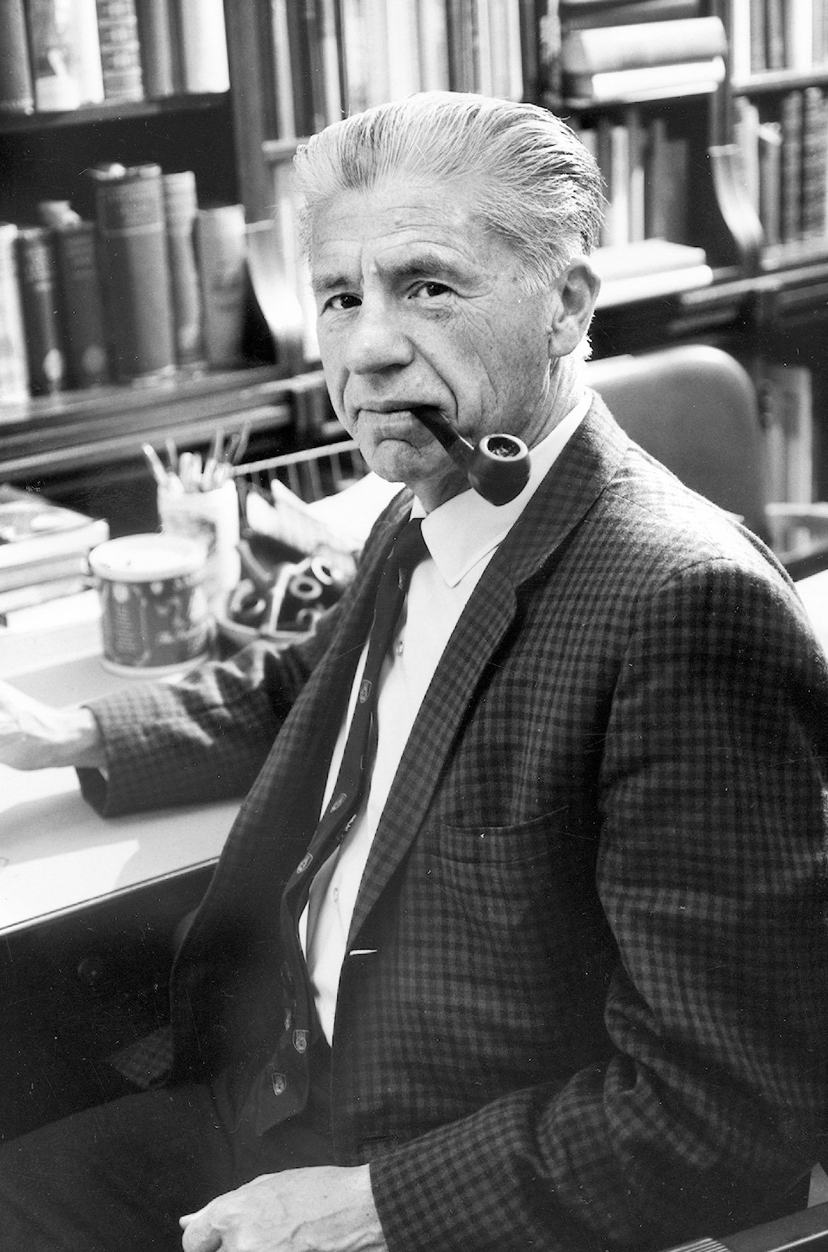
M.H.艾布拉姆斯
理论写作之外,艾布拉姆斯还是一名杰出的文学教师。1945年,他成为康奈尔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及小说家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都是他的学生。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布鲁姆开始了他对“西方正典”终身的痴迷。而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艾布拉姆斯的浪漫主义研究中,求得教益。因其著作,描绘了一个激荡时代中的思想嬗变,正如我们所生活的当下。
以浪漫主义为抓手,鸟瞰西方文论
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于1953年出版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时常出现在中文系必读书单中,以作本科阶段的文学理论入门之用。该书的第一章,可能是其最被广泛阅读的一章。它以提纲挈领的宏阔视角,将西方文论两千余年的历史,装入作品、作者、读者、世界四个象限。诸多理论的坐标,便在这四象限之内得到确定。
尽管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文论的研究专著,艾布拉姆斯却没有将视野局限于浪漫主义时期。《镜与灯》的理论野心,在于借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以降浪漫主义文论的透镜,重新检视那被无数或现代,或后现代,或激进,或保守的理论反刍过的对文学之本质的迷思,以在崎岖难行的词语幽径中,厘清其方向,确定其重量。故《镜与灯》上溯柏拉图(Plato)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典范,下及该书出版时1950年代的文学思潮。它为西方文论清理出一条由摹仿论到表现论的清晰轴线,浪漫主义文论正处于轴线的中心。即使艾略特(T. S. Eliot)之类自称反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文论家,也无不继承了浪漫主义文论对情感及艺术家主体性的强调。1800年,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所定义的诗歌,即那承载了“在平静时刻追忆起的强烈情感的”诗歌,构成了当代人对诗歌的想象。它应该是浓烈而简短的抒情,任何叙事及议论的杂质的掺入,都会像兑进醇酒中的自来水一样,改变词语的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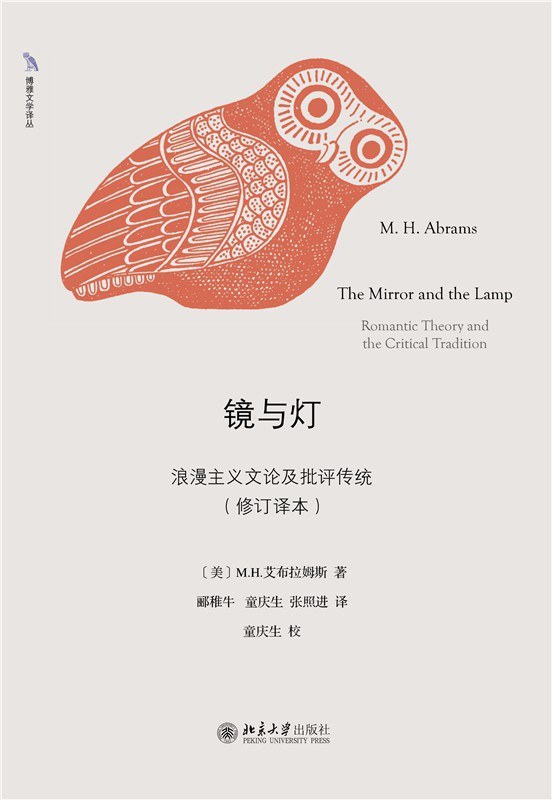
《镜与灯》
在《镜与灯》中,艾布拉姆斯以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写于1833年的两篇文章《什么是诗》《诗的两种类型》,来说明由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丕变。新古典主义者循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设下的理论路径,将史诗视作诗歌之王,将悲剧视为诗歌之王后。他们都认为,诗歌的本质,乃是对人类行动的模仿。密尔却强调抒情诗的重要性,认定其是“比其他类型更杰出更独特的诗”,在密尔眼中,那些只是“简单模仿或描述”某种行动的诗歌,甚至不能被称为诗歌,只有笼罩在“情感晕轮”中的诗歌,才值得被铭记,被称颂。诗歌的忠实,不再是如摄像机般将外部世界搬到胶片上的忠实,而是应该转向创作者的内心世界,透过这心灵的窗口,在外部世界中寻找“诗人内心状态外化的等价物”。在密尔这里,我们已可以看到象征主义诗学的滥觞,看到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物诗与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对于艾略特而言“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惟一途径是发现一个‘客观对应物’,换言之,发现构成那种特殊情感的一组客体,一个情境,一连串事件,这样,一旦有了归源于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情感便立即被唤起了”。
在密尔的论述中,遭到翻转的,不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的摹仿论。实用论的理论范式同样被否定。而在此之前,摹仿论与实用论,是构成新古典主义文论的两大核心观念。后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在《诗艺》中提出的“寓教于乐”。不过,在艾布拉姆斯看来,贺拉斯对诗歌感染力的强调,胜过对道德教化作用的强调。因此,从古罗马时期到18世纪,修辞学家们都竭力发掘词语的质感、速度与锐度,为之确立正确的用法,以使其能更高效地感染观众。他们为诗歌打造出格律的藩篱,为之划定清晰的疆界,不同的诗行长度即对应不同的文学体裁,悲剧的诗行应与喜剧的诗行大异其趣,两者的混用被视为离经叛道。在他们眼中,这些繁琐的规则就如同阿喀琉斯的盾牌,可以将整个世界收纳在诗歌的方寸之间,并使词语更坚实,更难以朽坏。
对于实用论,艾布拉姆斯以18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为例进行说明。尽管约翰生并非以抽象的文学理论进行创作,而是以其作为诗人的直观感受进入批评的场域,但这篇文章的确是新古典主义批评的里程碑。在其中,摹仿论与实用论被统一起来。约翰生写道,莎士比亚之所以受到读者的追捧,“除了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感的欲望外,别无其他原因”,但在娱人耳目之外,莎士比亚的永恒性质在于,他能够“给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以正确的表现”。经典必须能够表现世界本质的原则,同时打动那一时代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
但在密尔以及他之前的浪漫主义者眼中,读者变得无关紧要。密尔认为,“诗就是情感,在孤独的时刻,自己对自己表白。”它不再需要取悦读者,而只需遵循诗人内心深处的隐秘秩序。这一姿态可以见诸绝大多数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说:“我生平作的诗,没有一行带有公众的思想阴影。”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则认为,“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诗人的听众好像为了一个听得见却看不见的音乐家的绝妙声音而颠倒的人⋯⋯”
象征主义者虽然在语言与作诗法上颠覆了浪漫主义诗人,却继续了浪漫派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的做法。诗人成为被诅咒者,一如象征派鼻祖,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57年在其代表性诗集《恶之花》的开篇第一首诗作《祝福》中写道的,诗人的母亲诅咒他胎中的胎儿:“当至高无上的大能天神命令/诗人在这厌倦的世界上出现,/他的母亲惊恐万分,骂不绝声,/对着怜悯她的上帝握紧双拳://“啊!我宁愿生下的是一团毒蛇,/也不愿喂养这招人耻笑的东西!”不过,诗人却受到命运的垂青,能够以孩童般充满好奇心的目光进入这个世界:“然而,有一位天使的暗中保佑,/这个被弃的孩子陶醉于阳光,/在他所喝的所吃的东西里头,/又发现了美味和红色的琼浆。”
我们至今仍可以听到浪漫主义文论的回响。它左右着我们对诗人形象的想象。仿佛诗人不再是世俗之人,而是德国浪漫派画家卡斯巴·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画笔下的云海漫游者。他们是一管孤绝的芦笛,万物经由他们,发出悠扬的回声。尽管在后现代状况下,笼罩在诗人身上的浪漫迷雾正在被一层层地褪去,然而其核心,即那种对语言之纯粹性的孜孜以求,对创作之崇高性的确认,却得以保留。
架起浪漫主义与西方古典传统之间的桥梁
1953年出版《镜与灯》之后,艾布拉姆斯的另一部代表作《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于1971年付梓。相较广为人知的《镜与灯》,艾布拉姆斯本人更看重这本经过了十余年理论沉淀的著作。它延续了《镜与灯》的主题与考察视野,却更全面地回顾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成就。如果说《镜与灯》的关注点,集中在由摹仿到表现的书写范式转变,读者看到的是文学观念在时间侵蚀下结成化石的缓慢过程,《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则更注重观察浪漫主义文论的哲学背景,读者可以借此窥见彼时文学所处的思想地层,进而了解书写范式转变的成因。
该书中艾布拉姆斯的论述,与俄裔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其1965年所做的讲演《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所描述的浪漫主义思想图景,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认为浪漫主义是欧洲思想的一次根本性转折,也都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发现了英法两国浪漫主义的本源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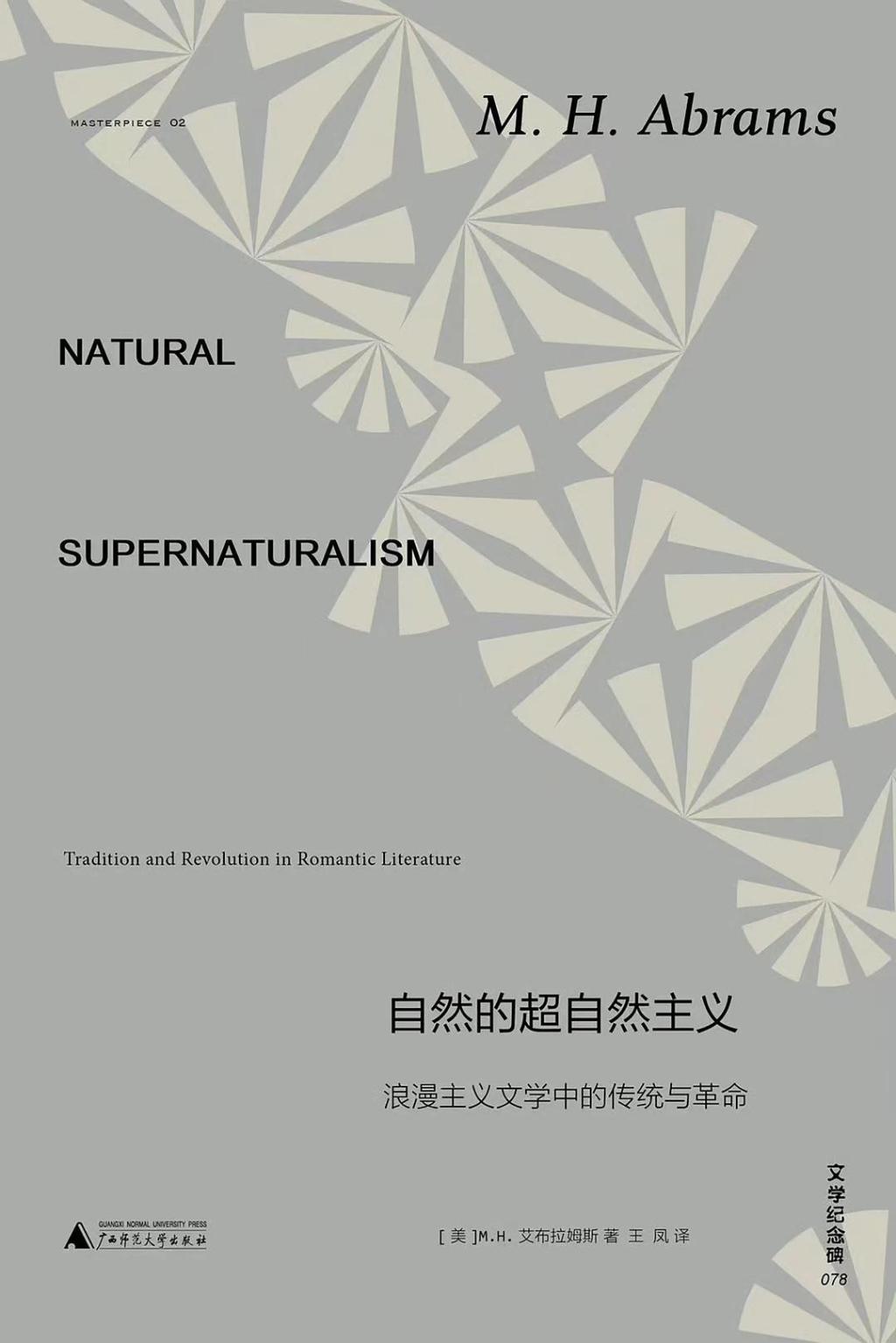
《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
伯林强调,“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观念。在我看来,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但他亦认为,浪漫主义的范畴是难以被确定的,其中总是存在着互相抵牾的观念,拜伦(Lord Byron)的激进与华兹华斯的保守几无相似之处,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是虔信徒,雪莱却在1810年写出《无神论的必然》一文,向宗教信仰发起挑战。他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如黏合剂一般,将纷繁复杂的浪漫主义观念碎屑结合起来的共同主题。而在18世纪德国思想家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那里,伯林听到了浪漫主义的最初胎动。正是哈曼,以其满溢着诗性的文字,质疑启蒙知识分子所笃信的理性与进步的价值。他虽非第一个这么思考的人,但在伯林眼中,在诸多反叛启蒙主义的18世纪知识分子里,“哈曼是最有诗意、最有神学深度、最能引发关注的代表人物”。
哈曼的思想,概而言之,是“一种神秘的生机论”。透过对神话的重新认识,哈曼发明了一种对自然的崇拜。在他看来,“神话是人类用来表达他们对于不可言喻的大自然之神秘的感受的,借此表达出他们无法用其他方法表达的感受”。由神话向语言的坠落,则意味着对人类“所面对的生命和世界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生机”的破坏,因为词语总是生产着意义,然而意义却只能归属于事物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断,人们并不能从词语中看到全部的事物。故词语总是非自然的,唯有诗歌能让词语回到原初的自然状态之中。
顺着伯林的分析,我们可以攀入《自然的超自然主义》的论述链条。在该书第七章《诗人的灵视:新旧大地》中,艾布拉姆斯将哈曼的日记与华兹华斯的长诗《序曲》并置,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发掘出“华兹华斯发现自己使命背后隐藏的传统”。与伯林不同的是,艾布拉姆斯认为,在以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忏悔录》为代表的忏悔文学,到浪漫主义诗人对自身使命的体认之间,存在着一条草蛇灰线般的联系。无论是哈曼,还是华兹华斯,都处在忏悔文学的阴影之下。这一文学的经典叙述方式,乃是主人公陷入强烈的精神危机,怀疑过往生活的意义,却又通过顿悟,或者长期的思想历练,重新发明一种自我认同,确立一套价值体系。哈曼透过重读《圣经》,发现了琐碎之物的价值,每一滴雨水都是一个小小的棱镜,折射出自然全部的神秘。无独有偶,华兹华斯也看到,作为先知的诗人,并非要承担沉重的历史责任,而是应该“用最生动的语言表达生动的思想/听从天生激情的命令”,以语言为平凡的事物加冕。
由此,我们便抵达了“自然”这一关键概念。无论在浪漫主义文学里,还是在现代及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自然”都是诗人对话的重要对象,诗人开始相信平凡的圣所,寻常的奇迹,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捕捉某个灵韵焕发的时刻。而要理解何以“自然”被单独框出,作为文学思考的母题,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宏观的理论视野。一如《镜与灯》以亚里士多德以降的摹仿论为参照系,《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将神学隐喻作为反思浪漫主义自然观的重要参考。在艾布拉姆斯看来,浪漫主义者们习惯于把神学概念世俗化为文学观念。对忏悔文学之叙述形式的广泛征用是一个典型例子。浪漫主义者在忏悔文学中发现了写作者内心生活的价值。而浪漫主义文学中广泛存在的堕落与回归的叙事,同样和西方古典传统异曲同工。譬如,在以诺斯替派为代表的神秘主义传统中,宇宙最初是统一的,随着这统一的瓦解,恶开始出现,嗣后,在历史终结之时,一切都将回归统一。浪漫主义者继承了这一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叙述形式。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消解了统一的绝对性。统一不再是完全的一律,而是在多元共振的前提下,重建某种共同的秩序。宇宙重新被纳入一个系统,然而这一系统虽已成型,却仍在不断地流变、更新,重塑着其躯壳,其疆界。
诗人若要从尘埃中捕获意象,就应该有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建立某种秩序的能力。而透过诗人内心的秩序,他发明了属于自己的“自然”。诗歌写作由此成为一种小型的历史循环,起初,一如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所歌诵的,“词语破碎处,无物可以存在”,人们语言使世界原初的和谐与统一陷入分裂,然而,诗人有一双“倾听之眼”,可以看见万事万物内在的韵律,并将之形诸语言。经由他的书写,语言中嘈杂的噪点得以融化,一个部落混乱的方言得以变得纯粹。因而我们要说,对写作者之语言使命的发现,可谓浪漫主义最深刻的思想遗产。之于我们这个词语爆炸,但语言贫瘠的当下,诗人的这一使命变得尤为关键,也尤为艰难。但突围的可能性始终存在,透过碎片、空白与缄默,当代诗人试图抵达语言的彼岸,在此一意义上,他们也如浪漫主义者们那样,成为了我们这个世代“不被承认的立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