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春秋战国时是齐文化占了上风,历史的进程会不会两样?
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绽放的第一个高峰期。从春秋至战国初期,齐国创办稷下学宫,广纳天下贤才。贤人高士无政务烦劳,却可享受士大夫丰厚待遇,所谓“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他们在这里授徒、问政、争鸣,将诸子之学推向巅峰,形成了百家飚骇、云蒸霞蔚、空前绝后的学术气象。先后有两位圣人级大儒孟子、荀子至稷下学宫。但春秋战国纷乱的历史,终因“上无贤主、下遇暴秦”,导致先圣在悲怆艰难的步履中走向生命的终结。
在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稷下先生》一书中,作者陈歆耕将笔墨聚焦于这一重大历史文化事件,融学术、史实、文学性表达于一炉,描画出稷下先生“奋髯横议”的宏大气象、顶天立地的坚挺脊梁、忧戚天下的悲悯情怀、穿越数千年时空的智慧光谱。下文为陈引驰为《稷下先生》所作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稷下学宫,是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一段华彩乐章。
战国时代的齐国,曾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齐据东方,与西边的秦国和南边的楚国,似乎构成了鼎足三立的格局。周振鹤先生《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比较齐、秦的差异,指出了历史展开的另外一种可能:
从文化样式而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发展优势......在差异颇大的多元文化类型中,要数秦、齐之别最大,......越是个体生产,越是离不开集权,一大堆单个的土豆只有靠袋子才能拎得起来,分散的、大量的小农经济,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与纳税的效能。因此根深蒂固的农本思想必然导致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而为了保证集权制度的正常运转,又需要被统治者的效忠,为此又必须采取愚民政策与文化专制主义。这就是秦文化的逻辑。反之,集体的、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以及沟通生产与消费部门,周流天下的商业活动,却需要开放,需要一定程度的地方与部门的分权,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不容易保守。这是齐文化的特点。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变局,一是春秋战国,封建改而郡县......郡县制的实质是将国家分成有层次的区域(行政区划)进行管理,变分土而治为分民而治,实现中央集权制,这是社会的进步。但集权过甚,则造成社会的停滞。在第一次变局之时,历史选择了秦文化,多元文化渐渐消融于小农经济的一元文化之中,如果当时是齐文化占了上风,则历史的进程会不会两样?
在历史学家的眼中,从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来看,齐国更具有多元的丰富性。稷下学宫正是这种多元丰富性的生动体现。

稷下学宫遗址
所谓稷下学宫,是齐威王、齐宣王、齐湣王、齐襄王等数代齐国国君支持,在国都的稷门旁建立的学术机构,汇聚众多饱学之士,给予丰厚的待遇,所谓“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一时称盛,《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述: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这么多的士人好住好吃,聚集在一处,“不治而议论”,就是不用他们管具体的治理政务,而让他们仅须各抒己见,众声喧哗。这真是士人们自古以来的美梦啊。
于是,无论那时候已成立或正在逐渐成形之中的儒、道、法、名、阴阳等诸家,都争相在此显山露水,各逞其能。比如儒家,虽然两位儒学大师观念上存在诸多差异,但荀子曾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孟子也曾游于此地,与稷下学宫中多位饱学能言之士有交集和论辩。不过依我看,稷下学宫在学术上最重要的成果的对“道家”的形成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荀子像
战国、西汉时代所谓的“道家”,并非仅限于我们今天所认定的老、庄之“道家”,更准确地说,当时的“道家”是指“黄老之学”。《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谈到西汉极为推重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有一段话:“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是说那些推重“儒术”的士人们贬抑“道家”,便自然引起偏好“黄老”的窦太后的强烈不满——从文字的对应上可以清楚地见出,“黄老”与“道家”是一回事。这一实指“黄老之学”的“道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之前,是西汉初年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哲学当然是具有非常现实的目标和实际的作用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评说那个时代的“道家”的时候,说它“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史记·太史公自序》)。
“黄老之学”的政治哲学,最简要的概括就是:虚实相应,动静结合,总揽分任,顺势而为。其中,“顺势而为”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其实就是汉代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的观念基础。至于“虚实相应,动静结合,总揽分任”,不妨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刘邦驾崩后吕太后势力一时笼罩天下,待她去世,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汉文帝即位。汉文帝原先是位很边缘的宗亲子弟,刚从自己的封地来京城,一时弄不清状况,后来逐渐明了,很关心国家到底是怎么治理的,于是就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周勃是武将出身,不晓得答案,几个问题下来,很紧张,汗流浃背。文帝于是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回答得非常清楚:“‘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穀,责治粟内史。’”所谓“有主者”,就是说皇帝想知道什么事情,直接去问负责的人就好了。于是文帝就很奇怪,便问:“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这些事都有负责的人,那要你做什么呢?陈平回答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陈平的回答非常典型,代表了黄老政治哲学的原则:宰相是总览全局的,虚而不具体做事,底下的官员才是实而干实事的。这一认识和态度,用较抽象的理念来表述就是:上无为而下有为。
这一理念早在稷下学宫这里已成为基本的认知。司马迁曾提到,活跃于稷下学宫的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的文字里就明确提到君臣上下之别:“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为焉。”(《慎子·民杂》)对稷下之学而言,还有一部归名于齐国早先的重要人物管仲的书,但这部书如今都认为绝不能认定是管子个人的著述,而是齐学尤其是稷下之学的渊薮,《管子·君臣》篇也非常清楚地将上下君臣的责任做了区分:“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由此可见,稷下之学对后世的政治现实有非常重要的先导、启示。这其实也非常符合古时对稷下学者的认识:
《史记·孟荀列传》:“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新序·杂事》:“稷下学者喜议政事。”
《盐铁论·论儒》:“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
《风俗通义·穷通》:“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
其实从先秦的百家争鸣以下,诸子的学术,都有着现实的面向,蕴含着他们的淑世怀抱,西汉初年《淮南子》就清楚地指出,诸子之兴起,是为“救世之弊”(《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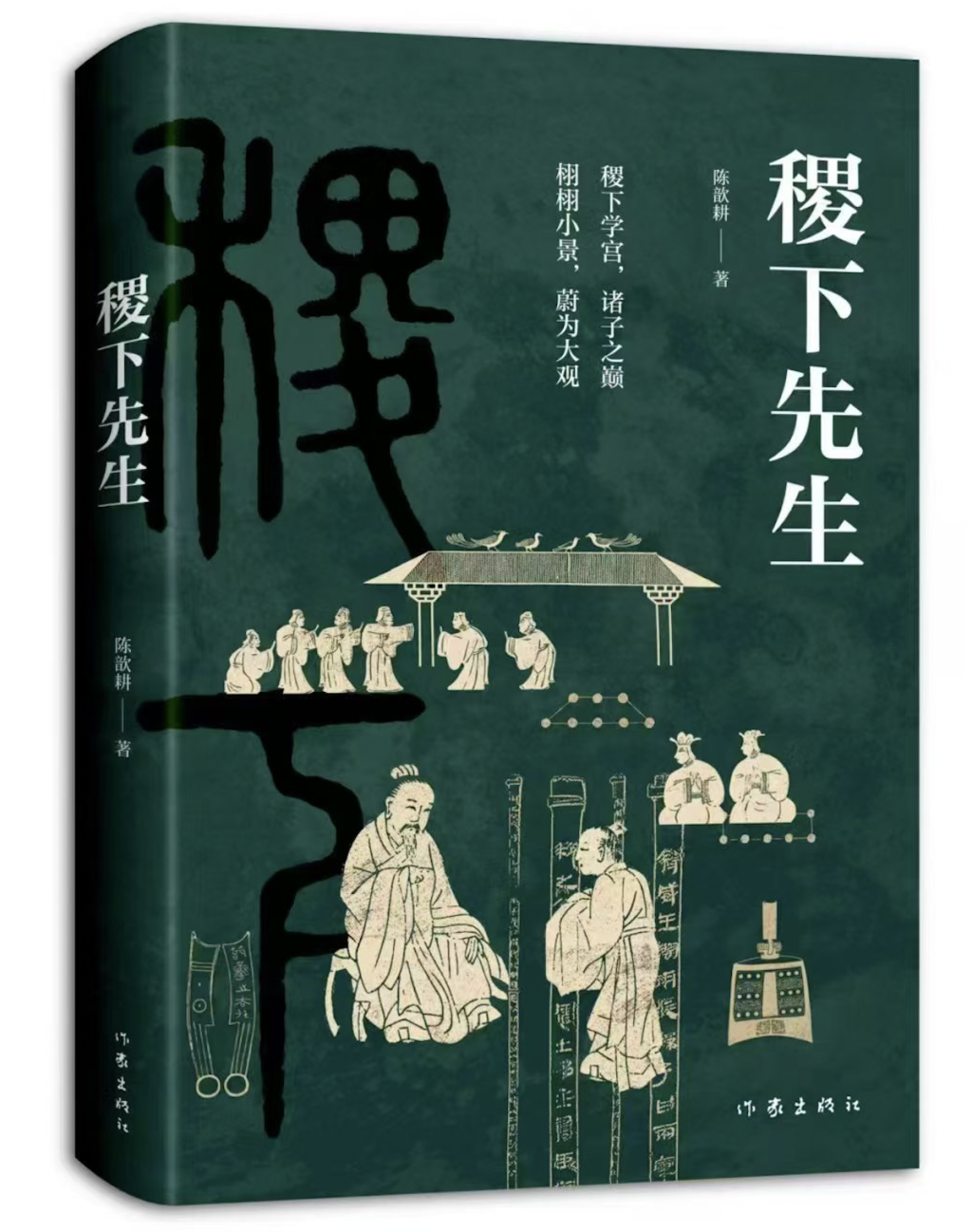
《稷下先生》
由此而论,陈歆耕先生所著的《稷下先生》在梳理了“稷下学宫”的历史始末等基本情形之后,即首先着力写叙“面‘刺’寡人”部分,指明稷下学者们:
有的人着力探讨形而上的宇宙问题,个体生命最佳的存在方式、修身之道。但更多的人着眼于探索天下兴亡、盛衰的内在规律,力图使自己的才华、智慧有益于世。
是非常之允当,抓住了关键的。
其后,歆耕先生自然不废稷下先生们多样丰富的学术思辨,有根有据,一一道来。特别值得提出,歆耕先生此书,灵活自如地调用了各种子书、史籍,缀合、勾画了稷下智者们的言谈、举止,细看是一幅幅小景,但统而观之,则蔚为大观,具体而全面地展示了稷下学宫的智慧生活。
不唯此也,歆耕先生接着浓墨重彩书写了与稷下学宫相关的学者之中最有名也最重要的两位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在稷下学宫的背景下,孟、荀的思想形象得到更鲜明的突显;因两位的存在,稷下学宫更得到高光的呈现。最后的“断简残章”,应该说是作者太过谦逊的命名,在这一部分,他放开眼光和思想,笔下扩至更多的诸子大家,心意更升腾至士人在文化之中的价值和意义,许多歆耕先生的自家体悟和意见,或许很值得读者鉴察。
我与歆耕先生相识既久,往还实少,最深刻的印象乃恂恂君子。今拜读《稷下先生》大作,更真切感知到作者为学之踏实恳切和内心情思之激越。承歆耕先生青睐,邀晚生为序,不能辞,谨述学习之后的感想与印象如上。
(陈引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文系主任(2012-2020),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道家思想与文学、中古佛教文学、近现代学术思想、海外汉学等。)